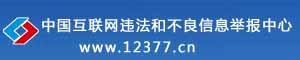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研究中,对以分裂当今主权国家为最终目标的民族分离主义的相关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刘泓研究员长期从事世界民族问题研究,成果颇丰。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的《当代国外民族分离主义与反分裂研究》(以下简称《当代》),是刘泓及其团队在民族分离主义方面的又一力作,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成果,该书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一、中观的研究视角
在世界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刘泓一贯坚持一种冷静的中观视角,将视野汇聚在世界民族的热点区域,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对个案进行梳理分析,并根据政治学相关理论提出应对策略。她在《欧洲联盟:一种新型人们共同体的建构》一书中,从欧洲的历史事实和欧盟的现象出发,着力阐述欧盟作为一种区域性人们共同体建构的现实意义,以及从结构化的视角对欧盟的未来发展进行集中探讨。这本书也被收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法学社会学研究系列之中。这一次,刘泓将目光投射在民族分离主义与应对策略之上,以多年来对国外民族分离问题的现实进行跟踪分析为基础,将其长期以来的研究探索成果以《当代》的著作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作者观察到,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民族分离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施加影响,试图改变当前“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在国家建构较为健全的国家,民族分离势力采取和平诉说的方式,博取民众的支持和同情;而在制度发展不完善的后发型国家中,民族分离势力往往借助暴力恐怖的方式施加压力。尽管方式有别,但民族分离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分裂主权国家,不仅严重影响相关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而且对地区安全和国家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趋势都构成了挑战。
《当代》的探讨对象汇聚在国外民族分离主义的多项个案之上,再针对性地提出反分裂的理论与策略方面下功夫,重点是对民族分离主义的非理性进行揭示,对反分裂的合理性和现实策略做出阐释,完成了一个学术命题的自恰性研究。作者在书中将国外民族分离主义的表现形式总结为暴力恐怖手段(北爱尔兰模式)、军事对抗手段(科索沃模式)、政治运动手段(魁北克模式),分离势力籍此与主权国家的中央权威进行互动,在不同程度上威胁到了相关“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性和社会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并未困于民族分离主义的个案窠臼之内,作者将视野扩展至民族分离主义的普遍运动趋势之上,期望通过结构化视角和反思性历史事实,借由人类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对现行“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框架下的民族分离主义模型形成新的阐释。这不仅有别于西方学界针对民族分离主义的概念性探讨,也为我们应对民族分离主义以及民族团结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二、独到的分析
在《当代》一书中,作者以民族分离主义的种种模式为突破口,渐进性引出研究的主体。在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之中,一直存在着一个争论的主题,即是否能用绝对的民族同质化应对民族分离主义。在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之中,此类尝试并不乏见。然而《当代》一书指出,以绝对的民族同质化应对民族分离主义,并不具备实践理性。刘泓认为,民族分离主义和绝对的民族同质化本质上欧洲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家设想的“国族-国家”观的一体两面。她为此梳理了法德两国早期民族主义流派的主要思想,指出,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形成民族共同体自我认同的社会划分观念,一方面民族主义调动了人类心理的认同本能机制,极大程度的整合了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社会框架;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对于区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定标准过于自由、笼统,以至于“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差异,也被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拿来塑造族裔认同”(第477页),从而为民族分离主义和绝对的民族同质化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于是,“分离主义者可以以任何差异为由,要求另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族-国家”,而同化主义者则可以凭借文化同质的借口,“对具有差异性文化的人民进行同化。”(第479页)
此外,作者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主体界定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刘泓认为,民族主义运动具有特定主体和实效性的特点。“当今世界的国族-国家,普遍是以某个相对强大的人民为基础,连同一些与之联系紧密的相对弱小的人民共同体建立的”(第481页),正是在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各民族的努力之下,经过了不懈斗争,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这是“各族人民生活之渠交汇流淌的结果,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496页),因此,在殖民时代已然成为历史的当今世界,绝对的民族同质化与民族分离主义收到普遍的否定,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刘泓进而提出,当今世界各国根据各自国情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包括民族联邦、民族文化自治、民族区域自治、保留地制度以及综合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既是各民族共同体内部利益妥协的必然结果,也是以尊重差异为基础的一体化政策。由此,读者可从中窥见民族分离主义与绝对的民族同质化的对立统一以及二者之间可以进行政治沟通的间隙。
在《当代》书中,作者颇多具有启发性的论断,其火花不在于类结论导向似的“单向解构”民族分离主义,而是希望读者能从民族主义的作用和民族国家建构历史事实中形成“反思平衡”,具备面对分离势力以及国族一体化进程中具有抉择能力的理性思维。《当代》一书中的诸多案例分析以及诸多独到性的创见,有利于读者体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在政治光谱的每一面,我们都能看到对社会断裂的担忧,以及对于复兴共同体的召唤”[1]。只有建立各族体之间的有效的沟通和协商机制,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家国格局。
上一条:
下一条:

 蒙公网安备15030202000257号
蒙公网安备15030202000257号